
这片山野便是洞霄宫遗址 (本版图由夏斯斯提供)

洞霄宫遗迹碑

九峰拱秀牌坊

会仙桥上的刻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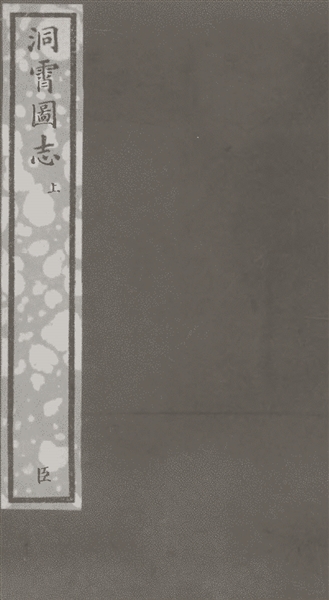
《洞霄图志》书影

元同桥
夏斯斯
天目山脉迤逦东展至临安与余杭交界,曾有一处道教名胜坐落其间,名曰洞霄宫。它的渊源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辟为祈福之所,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奉敕建天柱观,唐昭宗乾宁二年(895)钱镠改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奉敕改名洞霄宫,到两宋发展最盛。
历史上的洞霄宫别有一番景致,美轮美奂,气象恢宏,更兼文人墨客,名士云集。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巨、影响之大,在海内屈指可数。时移世易,昔日的盛况已烟消云散,只剩下荒烟蔓草、故道残阶。这片青山旷野间竖立的“洞霄宫遗址”文保石碑,默默诉说着那穿越千年的繁华与落寞。
将“洞霄”二字安在
杭州的这座宫观之上,有何深意?
“洞霄宫”之名定于宋代。《洞霄图志》云:“宋真宗祥符五年,因陈文惠公尧佐奏,改洞霄宫。”宋真宗在位时开创了咸平之治,后期则任用宰相王钦若,伪造天书,大兴祥瑞,广建宫观。在自导自演的“天书”闹剧中,真宗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启封宣读“天书”,还密谕辅臣:“凡有祥异即上闻。”
大中祥符五年(1012),陈尧叟的弟弟、两浙转运副使陈尧佐造访天柱观,见到“五色云”“地涌泉”等异象。观外有一株大栎木,“相传唐咸通二年吴天师所种”。“吴天师”据说是唐代名道吴筠(?—778),然而咸通二年(861)这位吴天师已经“仙去”,这树是他怎么种下的,令人摸不着头脑,总之大有来头便是了。到了宋咸平元年(998),这株大栎木无缘无故地枯死了;十多年后至陈尧佐来天柱观时,又莫名其妙地枯而复荣。陈尧佐将上述异事画成图状,表奏朝廷。宋真宗果然喜闻乐见,特赐“敕赐洞霄之宫”六字宫额,并赐田十五顷以奉斋醮(一种道教仪式)。
“洞霄”之名从何而来?其实是从别处“复制粘贴”来的。在此之前,他处已有洞霄宫。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光宅元年(684),临朝称制的武则天追尊老子之母益寿氏为先天太后,在亳州建宫观以祀奉,其名即“洞霄宫”。三百多年后的北宋,亳州的这座洞霄宫仍在,据《宋史·真宗本纪》,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二十二日,宋真宗驾临亳州洞霄宫,还撰有《先天太后赞》。
将“洞霄”二字安在杭州的这座宫观之上,有何深意?让我们回到“祥符五年……改洞霄宫”这个时间点,这一年,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宋真宗力排众议,册立爱妃刘娥为皇后。
真宗对刘娥深为倚信,把唯一的皇子养在无所出的刘娥名下,还让她陪伴左右处理政务,无形中在为她成为宋代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而铺路。昔年武则天追尊老子之母,将先天太后与“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同庙奉祀,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抬升自身地位的政治需要。若照此思路揣测,宋真宗重提“洞霄”、赞颂先天太后的用意,大概也可以呼之欲出了。
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之后,曾有亳州、杭州两座洞霄宫并立的情况。改名之后的杭州洞霄宫虽说像个“后起之秀”,但从西汉算起,它已然是千年古观。依凭深厚的底蕴和难逢的良机,它很快一骑绝尘,地位超然,逐渐独占此名。
从“宫宇颓圮”到“天下宫观之首”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余杭籍的洞霄宫住持都监何士昭因宫宇颓圮,来到汴京陈乞。徽宗赐度牒三百道(度牒可免除赋税、劳役),令两浙转运司经办,将洞霄宫修葺一新。但在随后的方腊起义中,洞霄宫不幸毁于兵燹,直至宋室南渡后才斥资重建。《嘉庆余杭县志》载:“洞霄之名始于宋,而其迹实肇于汉,恢于唐,至宋南渡而称极盛。”
南宋初年,临安府余杭县的百姓们惊讶地发现,大涤、天柱两山之间,仿佛在一夜之间出现了一片金碧辉煌的建筑,好似从天而降,又像拔地而起,恍若凡间琼馆,香烟缭绕,悠悠磬声回荡云霄。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余杭成为畿辅(注:京城附近)之地,洞霄宫地位日尊。绍兴二十五年(1155),宋高宗赵构以皇太后韦氏的名义,派修内司工役和步军司官兵重建洞霄宫殿堂,包括昊天殿、钟楼、经阁等,修缮费用皆出自慈宁宫私帑,人员、物资调度都未惊动地方官员与百姓,故而山麓之民晏然,都不知有劳役。落成之日,“金碧之丽,光照林谷”。
乾道二年(1166),为庆祝建成,太上皇赵构与太上皇后吴氏临幸洞霄宫,驻跸累日。此后,皇室成员又数次游幸洞霄宫,使之成为皇家行宫。为出行方便,还专门修建了西溪辇道。从杭州城西沿西溪路接102省道,正是当年由都城前往洞霄宫的专用御道。
南宋临安有十三大宫观,除了“位处皇城及西湖左近”的十二座(西太乙宫、东太乙宫、万寿观、德寿宫、景灵宫、佑圣观、显应观、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开元宫、龙翔宫、宗阳宫)之外,便是位于临安附近余杭大涤山的洞霄宫。十三大宫观是南宋皇家内祠,洞霄宫则是皇城之外唯一的内祠,可见其在皇家祭祀体系内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宫观”是道宫、道观的合称,一般来讲,道宫的规格要高于道观。钱俶纳土归宋时,为提高天柱观的地位,曾有意将观升格为宫,但宋廷并未应允。
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洞霄宫都监潘三华等人请陆游撰写碑记,陆游当时76岁了,身体欠佳,并未答应。同知宫事王思明等人再次邀约,陆游又因为编修国史抽不开身。直到嘉泰三年(1203),修史告一段落,陆游终于有空,作了《洞霄宫碑》。
碑文称,“洞霄宫……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宫独为天下宫观之首”“其地望之重……它莫敢望”。嵩山崇福宫初名万岁观,创建于汉武帝元封年间,宋代改名崇福宫,不仅是名儒往来之地,也是历代著名道教学者栖身传教之所。南宋时期,地处中原的崇福宫已在金国治下,《洞霄宫碑》所言的两宫并驾齐驱,不过是一场文字上的粉饰,实际上洞霄宫独领风骚。
天下神仙府,地上宰相家
宋元之际,钱塘(今杭州)籍思想家邓牧的《洞霄图志》载:“浙右山水之胜,莫如杭;杭山水之胜,莫如天目;天目之胜,莫如大涤洞天。”大涤洞天因“此山清幽,大可以洗涤尘心”而得名,位于洞霄宫遗址以西两百米处,今杭州市临安区境内。洞霄宫遗址旁,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洞霄宫村,与余杭区中泰街道九峰村隔小溪相望。
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大涤洞天为三十六小洞天之一,天柱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故而常认为两山之间的洞霄宫集洞天福地于一体,这是其他宫观无法比拟的。淳祐七年(1247),宋理宗御书“洞天福地”匾额以赐。
所谓“洞天福地”,是道教传说神仙所居的名山胜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是否有神仙到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洞霄宫的留名与凡尘之中的名人脱不开钩。大凡风景名胜,总是要与人物产生关联,才更有话题性。
洞霄宫作为皇家行宫,常得皇室成员光顾自不待言,宋代还有“提举洞霄宫”一职。这职务是个虚衔,坐食俸禄而不管事,多为安置“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的高级冗官闲员而设。宗哲宗时的宰相章惇一度被贬,提举洞霄宫,作诗自称“洞霄宫里一闲人”,号“大涤翁”。两宋官至朱紫(喻高级官员)而提举洞霄宫者,有百余人。
宋徽宗即位初,原任户部尚书的蔡京被罢免,提举洞霄宫,居杭州。他不安于做洞霄宫里的闲人,无时无刻不在谋求起用。潜心揣摩了徽宗的喜好,蔡京断定,凭自己挥毫落纸的功力,只要一股好风,就可以送他上青云。当时,供奉官童贯为了替徽宗搜罗书画奇巧,从汴京一路南下来到杭州。自诩为“地陪”的蔡京日夜与其寻欢作乐,持续数月。童贯也投桃报李,将蔡京所书的屏障、扇带送达禁中,并附以溢美之词,呈至御前。徽宗由此属意蔡京,继而委以要职。蔡京步步登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蔡太师。提举洞霄宫期间是他的韬光养晦之时,洞霄宫见证了他的东山再起,却也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他的晚景凄凉。
这些提举洞霄宫的宰执大臣,令此地有“天下神仙府,地上宰相家”之誉。更多的提举们则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比起帝王游赏的轻松惬意,其心境往往更为落寞。这里的长松流泉、磐石丛竹,究竟能否洗涤他们的尘心?
君从孤山来,秋思落谁家
没有文人墨客的洞霄宫是不完整的。古代的文人与官员,其身份常常会重合。比如苏轼,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他在杭州通判任上,游览洞霄宫并留同名诗一首,首句云“上帝高居愍世顽,故留琼馆在凡间”。两年后,他在密州知州任上作《过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写下这些诗篇时,他内心的天平究竟偏向哪一层身份,见仁见智。
有一个文人把官员的身份剥离得很彻底,那便是北宋钱塘人林逋。他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婚不仕,偕“梅妻鹤子”而终老,卒谥和靖先生。生性恬淡的他活成了一位纯粹的诗人,与洞霄宫“风清气和”的气质十分契合。
某年秋日,林逋从西湖孤山一路向西,至大涤山碧涧青林间,感受高秋的清美风物,还在洞霄宫住了一晚。夜里下起了雨,雨落在门外的芭蕉叶上,引人遐思。林逋写下了《宿洞霄宫》: “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
秋山无尽,秋思无垠。碧绿的山涧中漂流的红叶,不知要把这片深情传至何处。苍翠的树林间点缀的白云,也许让他想起南朝道人陶弘景的小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已是日落时分,飞鸟归巢,暮蝉乱唱,秋声满林。芭蕉更兼细雨,点点滴滴到黎明,何人在枕上漏夜聆听?答案也许是“无人”,毕竟这份闲适心情,“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北宋诗人梅尧臣评论林逋的诗“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林逋另有《洞霄宫》诗一首:“大涤山相向,华阳路暗通。风霜唐碣久,草木汉祠空。剑石苔花碧,丹池水气红。幽人天柱侧,茅屋洒松风。”看样子也是写于秋天,灵感可能就来源于夜闻芭蕉雨的那次行程。留宿于此的幽居之士,在洒满松风的茅屋里辗转反侧,不知秋思落谁家。与“茅屋洒松风”一比对,“此夜芭蕉雨”或许未必是真的雨,而是萧瑟秋风摇动芭蕉的沙沙如雨之声吧。
越陌度阡,回望千年
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腊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洞霄宫烧燎一空。同年早些时候,度宗驾崩,四岁的皇子赵㬎即位,是为宋恭帝,由太皇太后谢道清垂帘听政,她是二十七年前为洞霄宫御书“洞天福地”匾额的宋理宗的皇后。恭帝即位仅几年后,南宋灭亡。
穿越宋元的烟月和明清的风霜,洞霄宫屡经复建、损毁、灾变,终究侵圮殆尽,唯存遗址。2019年3月26日,洞霄宫遗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6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洞霄宫遗址名列其中。
从山口“九峰拱秀”牌坊而入,行经会仙桥、元同桥等,即抵达洞霄宫遗址。如果不是看到那两块文保石碑,我们很难将此地与昔日的“天下宫观之首”联系起来。据《洞霄图志》,会仙桥为“宋淳熙甲辰,道士江安著以早游湖海,晚岁归隐山中,舍衣钵钱重造”。元同桥原名玄同桥,得名于唐末道士闾丘方远(号玄同),“宋淳熙甲辰锦城盛氏施钱重造”,其上刻有“淳熙甲辰”字样,系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的遗存,清代为避康熙皇帝名讳更名为元同桥。
阡陌纵横间,往事越千年。周边的村落多已搬迁离去,这片充满故事的山野教人顿生“故垒西边”之叹。如今,随着第二绕城高速公路、火车西站的建成,杭州的城市建设不断向外辐射,位于西湖区以西,临安、余杭、富阳三区会际之处的洞霄宫可谓极具潜力的开发对象。未来,这里是否会出现一座新的文化地标?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