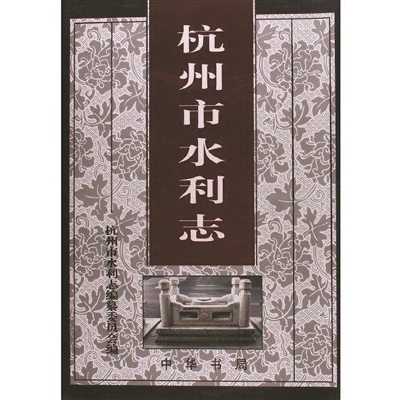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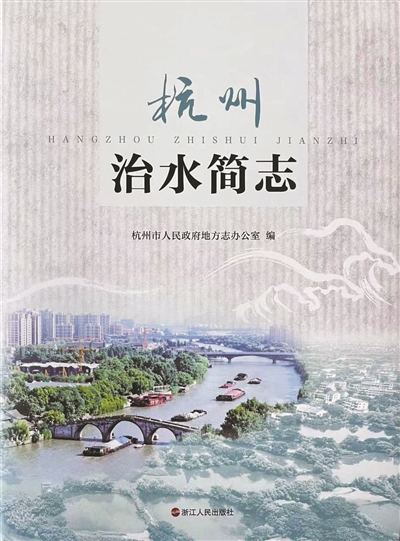
马琦敏
两千多年前,《史记·河渠书》开创了后代官修史志撰述水利专篇的典范,堪称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司马迁在记述了自上古至秦汉时代的重大水利事件后,写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除水之害,兴水之利,自古皆然。对于杭州而言,水是生命之脉,亦是这座城市的灵气之源。一部《杭州市水利志》,再加一部《杭州治水简志》,也就构成了杭州版的“河渠书”“水经注”。
兴修水利 代有所为
八千年前,跨湖桥先民排水辟田;五千年前,良渚先民兴建堤坝。先秦以来,杭州兴修水利,更是不遗余力,代有所为,开运河、治苕溪、浚湖陂、修海塘……始建于东汉的余杭南湖和西险大塘、贯通于隋代的江南运河、始筑于唐代的余杭北湖、开辟于宋代的萧山湘湖等水利工程,千载不废,至今仍发挥着防洪、航运、灌溉等重要功能。而唐代开引西湖水入城的“六井”、所筑西湖之堤“白堤”,五代始筑的“钱氏捍海塘”,清代的钱塘江鱼鳞大石塘等水利工程,因守护杭城千百年来的岁月安澜,总是令人怀德景仰。
在历史长河中,杭州官民与水抗争、对水治理、借水发展的智慧与才华,是杭州治水的独家记忆,滋养着杭州的人文情怀,联结起白居易、钱镠、苏轼、杨孟瑛、李卫等人一脉相承的治水功业和精神感召。十年前,杭州开始全面推行河长制。如今,河湖长制在实践中正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但其实,翻阅两部志书的大事记部分,我们会发现,那些因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兼任“河长”“湖长”的官员数不胜数,不止有“苏轼”。
前仆后继 争当“湖长”
比如,“程门立雪”中的主人公杨时,就有两条大事记。一是他在余杭当县令时,不畏权臣蔡京,阻止他欲占余杭南湖形胜之地以葬其母,守住了南湖。二是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近花甲的杨时又调任萧山当县令,当时县城周围农田易涝易旱,连年遭灾。杨时率领百姓,历时一年多,“筑堤围成湘湖3.7万亩,周长80公里,灌九乡田14.68万亩”。湘湖,由此“出圈”。在这位“湖长”的影响下,此后的地方官员前仆后继争当“湖长”。
再如,《乾道临安志》的编撰者周淙。熟悉的名字让我驻足细读,才发现他也是位矜矜业业的河湖长。南宋乾道三年(1167)五月,周淙任临安知府。眼看着临安城内,因居民日增,河流狭窄,行舟不畅,周淙便请求对河道开展治理。他先组织政府出钱,召集民众,浚治城内外运河,疏通淤塞,计6250丈。同时,又设立巡河办公点30处,撩河船30只,以此加强日常管理与浚治。“人谓其计虑深远,以治办称之。”“治办”的意思简单来说,便是“干得不错”,要是放到现在,估计会被授予优秀河长奖的光荣称号。治理完河道,他又开始马不停蹄地治理西湖。当时的西湖是杭城最大供水源,却遭到严重的人为污染,此前虽多次下令,禁止向湖里倾倒秽物,但收效不大。周淙奏禀宋孝宗降旨,“增设撩湖军兵一百人”“禁止抛弃粪土,栽植茭菱,及浣衣洗马,秽污湖水”“或有违犯者,许人告捉,以违制论处”。这样看来,周淙除了自己当河长,也欢迎民间出现河长,参与其中,保护饮用水源。在疏浚西湖的同时,他又修葺了引流西湖的唐代六井,为城内百姓饮水提供了保障。
也是这样一小段历史,让我们感受到,从一千两百余年前唐代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建六井,解决百姓饮用水咸苦之难事,到如今润泽民生的千岛湖配供水工程,让杭城百姓喝上家门口的“农夫山泉”,这一路走来,杭州的饮用水“有点甜”之路,跨越时空,向我们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
记载史册的“河长”还有许多。杭城百姓也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铭记着他们,或立碑题刻,或修祠造景,或以其命名堤坝等等不一而足。萧山有句俗语,叫“沿江十八庙,庙庙供张公。”这位张公,便是北宋朝廷命官、萧山人张夏,他开创性地以石塘代替土塘和柴塘,筑成坚固的海塘防线,深得民心。他殉职后,历朝念其修堤功绩,多次追封。从此,这位治水英雄便被沿岸百姓敬奉为“潮神”,一直铭记至今。在萧山衙前,距离古海塘不足百米的“张夏行宫”,成为历代百姓祭祀张夏的主要场所,而延续千年的“张夏祭”也被列为第七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善治国者必重治水。回望历史,从大禹治水定九州到如今,四千多年来,我们跟水的博弈、共存,从未停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治水也仍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将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