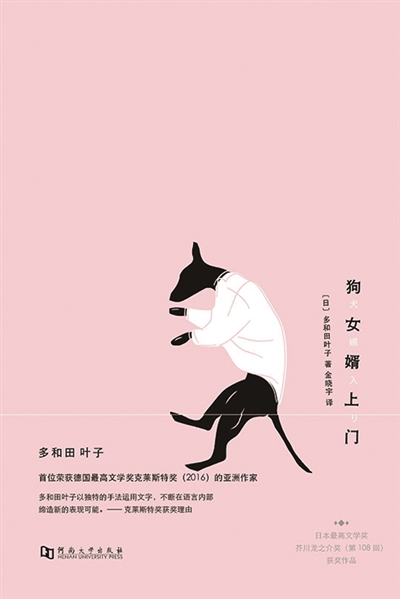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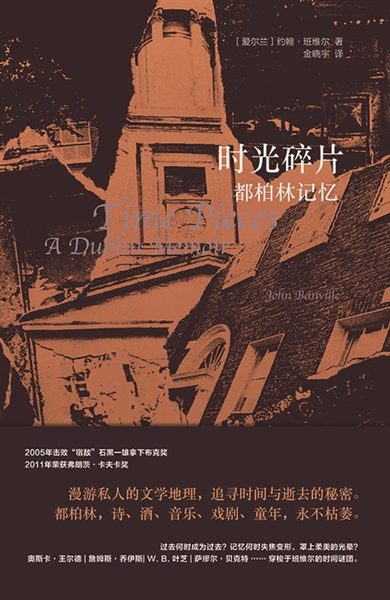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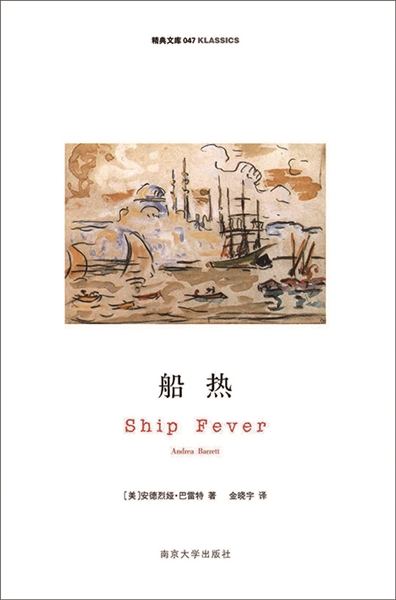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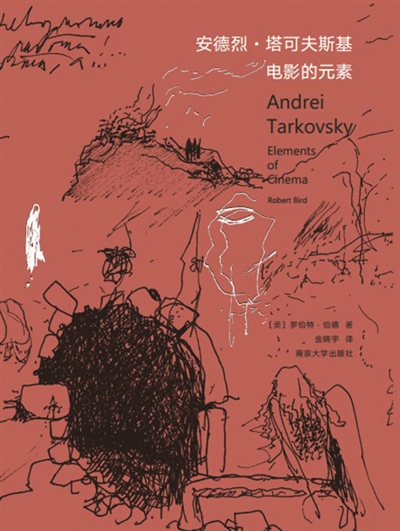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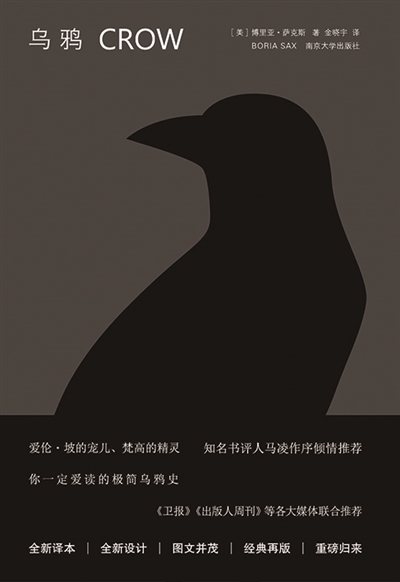
记者 潘卓盈
1月17日,一篇来自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栏目的文章《我们的天才儿子》刷屏了无数人的朋友圈。
杭州老人金性勇自述,他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的老伴刚刚去世,而他的小儿子金晓宇还在精神病院里(目前已经出院),“你们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里,他妈妈今天刚走了。”
金晓宇幼年不幸留下眼部残疾,后来又确诊为躁郁症患者,翻译成为他和命运抗争的唯一武器。这个残酷而温柔的故事,让全网读者都无之不动容。
相比作家,译者更像是文学作品背后的“隐形人”。能被读者记住的,实在凤毛麟角。被人称为“天才翻译家”的金晓宇,翻译的绝大多数外文作品,并非畅销爆款,甚至,有些非常小众。一夜之间,这位生活在杭州,很少被人知晓的译者,突然从沉默的隐形人状态,浮出水面。
金晓宇涉猎广泛,欧美小说、日本文学、博物学、艺术、神话、电影史,都信手拈来。无数资深文学爱好者惊叹,喔,原来,我读过的这些书,是他翻译的。很多人感慨金晓宇笔下的译文“措辞精准”“语感很好,常常能碰到让人心动的句子”……
文字,当落笔的那一刻,无论作者,还是译者,似乎都隐藏着其背后庞大的人生密码。很多时候,读懂作品,才是唯一解锁的那把钥匙。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不如跟着杭州翻译家金晓宇的译笔,一起来读读,那些迷人而温暖的文学作品吧。
金晓宇,1972年生于天津,现居杭州,自由译者,从事翻译二十多年。英译中图书有《船热》《诱惑者》《写作人生》《嘻哈这门生意》《剧院里最好的座位》和《十首歌里的摇滚史》等;日译中图书有《狗女婿上门》《和语言漫步的日记》《飞魂》和《丝绸之路纪行》等。
《狗女婿上门》
[日] 多和田叶子 著 金晓宇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译文摘录——
午后的太阳光,亮晃晃地照射在纵横晾晒的衣物上。公共住宅区内,七月的这一天,没有一丝的风儿,在这潮湿憋闷的空气中,一位老者孑然而行,突然在道路的中间停下脚步,扭头看着斜后方,呆立不动了。接着,一辆砖红颜色的小汽车在横穿着跑过住宅区的途中,也像是没有力气了似的,在邮筒的旁边停住,不仅没人从里面走下来,而且不知是将死的蝉的叫声,还是饮食服务中心里机器的声响,总之除了从远处传来低沉的鸣响声之外鸦雀无声,时间是下午两点钟。
在阳台铁格栅的对面、能铺六张榻榻米的房间里,只见一个女人独自泡了茶,一边抚弄着膝盖的疮痂,一边时不时地凝望什么图像也没有的电视机屏幕。或者,去了文化中心的女人家里的厨房,窗帘只拉上了一半,从敞开着的另一半,能看见冰箱上面有只没吃完的苹果,上面还留有口红印。直到孩子们放学归来,去补习班之前,这一新兴住宅区就像人死绝了一般,笼罩着愁闷的气氛。在这住宅新村的一角,一大张脏兮兮的纸,像缠住不放似的,贴在一根电线杆子上。从一年前或者还要更早些时候起,人们就以为它快剥落了吧,然而,它并不掉下来,顽固地粘在那儿。北村美津子用粉红色记号笔写的“北村塾”几个大字,被雨水洇湿过,变得模模糊糊,因为纸张破损,电话号码什么的也只能认出一半来,而且,由于粘着鸽子的粪便,地图也变成黄色,看不清楚了。不过,在住宅新村里,凡孩子上小学或初中的母亲们,谁都知道该补习班的方位,所以即便地图看不见了,也没人觉得为难,这张小广告揭下来也没关系,但不知道是因为太脏,讨厌碰它,还是咋的,没有人特意去揭它。不管怎么说,在这一住宅新村里,自从住宅区文化形成以来的三十年间,有种传统已经扎根,那就是:虽然自己家里每天收拾得干干净净,可遗弃在外面马路上,令人作呕的东西,绝不会去碰。即使道路的正中央有被汽车碾得稀烂的鸽子,或是醉汉拉的大便,也只会认为收拾这些是市政厅的工作。就连这张小广告,在它变成碎片、飞散在空中之前,大概也没人愿意去碰它吧。人们漠不关心的程度竟如此之甚。
《时光碎片:都柏林记忆》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译文摘录——
过去是从什么时候成为过去的?那些以前仅仅是发生的事情要过多久才开始散发出神秘和超自然的光芒,标志它们已经真正成为过往了呢?毕竟,我们记忆中承载着的辉煌幻象,一度只是现在,平淡无奇、枯燥乏味、完全不值一提,除了一些时刻,譬如一个人刚刚坠入爱河、中了彩票,或者听到医生传达坏消息的时候。当我们把经验送进过去的实验室,是什么样的魔力才将其塑造和打磨出最后背影,珀西广场段大运河所呈现的光辉?这些问题都只是一个问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们就让我着迷,那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即创造物不仅包括我和我的附属物——母亲、饥饿、偏爱干燥甚于潮湿等——而是,一方面包括我,另一方面也包括世界:由其他人、其他现象、其他事物组成的世界。
这么说吧,现在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而过去是我们梦想去往的地方。然而,即使它是梦,它也是坚实和持续的梦。过去是一个用绳子拴住和不断膨胀的热气球,使我们在空中飘浮。
然而,我再问一遍,过去是什么?现在必须经历什么样的嬗变才能成为过去?时间的炼金术在一个明亮的深渊里暗自蓄力。
《船热》
[美]安德烈娅·巴雷特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译文摘录——
但是,我们曾经比双胞胎还要亲密,而现在,不管我们只相隔一条马路,还是远隔一个国家,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有关我们往事的这个版本解释不了我们现在这么的疏远。这种精神上的疏离不是匀速进行的,却是持续不断演变的。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
(美)罗伯特·伯德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译文摘录——
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回忆录《循规蹈矩》中,讲述他如何舍弃了音乐生涯,因为,不像他的导师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他缺乏完美的音高辨别力。大约五十年后,年轻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自己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狂热爱好者——同样放弃了音乐,最终选定电影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始终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吸引他去从事电影工作。然而,正是在这里,塔可夫斯基发现了他自己那种形式的完美的音高辨别力,表现为准确无误的审美灵敏度和对文化冲动的敏锐反应,这使得他七部故事片中的每一部都作为重大文化事件,在苏联和全世界引起共鸣。
塔可夫斯基成名始于《伊万的童年》(1962),这个项目好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万不得已才被托付给这位新手导演。塔可夫斯基的这部电影拍摄于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约瑟夫·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其流畅优美的拍摄方式是那个时期的苏联新浪潮运动中特别典型的。在西方,塔可夫斯基的处女作和其他电影一道,例如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飞》(1957)和格里高利·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1959),帮助人们出乎意料地瞥见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潜在的复兴,这种潜在的复兴表现在这些电影中年轻主人公们的身上,也同样表现在电影大胆、自信的审美态度上。在国内外,《伊万的童年》都捕捉到了当下的精神,在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塔可夫斯基发现自己在欧洲各大电影节受到赞扬,被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们讨论,并被推到苏联文化的最前沿。
《乌鸦》(丛书名:守望者·物灵)
[美]博里亚·萨克斯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译文摘录——
鸦科鸟类喜爱闪亮的物体,人们可能会争论这意味着智慧还是愚蠢,但这是鸦科鸟类与人类的另一个共同点。较小的鸦科鸟类,如喜鹊和寒鸦,尤其因为偷珠宝而声名狼藉。格林兄弟在他们搜集的德国传说中,讲述了在17世纪,一位腐败的官员是如何利用一只寒鸦一次偷一枚金币,最终从施韦德尼茨市偷走整个金库的。这种疑似“人类本性的”行为甚至可能使人们怀疑这些鸟是女巫的魔宠。乌鸦和人类之间的相似之处往往会导致敌意以及喜爱之情。像人类一样,乌鸦是杂食性的,尽管它们特别喜欢腐肉。索马里的一则故事讲述了鸟类如何集会来决定怎么分配世界上的食物。聪明的渡鸦建议,所有比它大的鸟应该吃肉,而比它小的鸟应该吃素。这个提议被接受了,但其他鸟儿没有意识到的是,这让渡鸦可以自由地吃任何东西。
但是在20世纪以前,全球的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属于农村,人们时常会看到乌鸦在啄食动物的尸体。最值得注目的是,人们会看到它们在战场上撕扯死亡士兵甚至是垂死士兵的内脏。它们甚至学会了跟在军队后面,准备美餐一顿。但是,想到被乌鸦吃掉有时会让人感到安慰,特别是在那些喜欢把生命视为生死循环的文化中。在波斯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尸体传统上被喂给鸟类。
吃腐肉导致乌鸦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与死亡密切相关。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对死亡的态度一直是复杂和矛盾的。它同时带来了恐惧和安慰。它可以被看作消亡,也可以被看作通往另一个或许更幸福的王国。所有这些矛盾心理也延伸到乌鸦身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传说都使它们成为生者的导师和死者的向导。